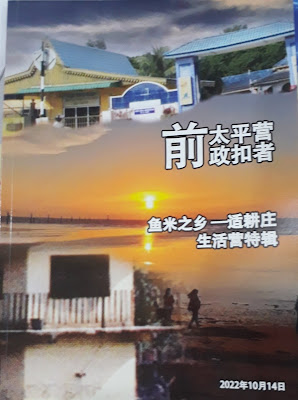抗日军“解甲归田”的历史真相

故事新编 日本投降刚过几天,盟军就在空中洒传单。有一份用中文书写,今保存在新山华族历史文物馆内。它的内容,首先吹嘘英美的武器比日本的威力大2千倍,然后说,英美的战舰已经在日本海域通行无阻,美军已把两座日本城市炸为废墟,等等。 英国人急着向老百姓汇报战情,不是因为他关心民瘼,而是要为他的重归造势。他的姿势高高在上,接下来他这样警告马来亚各民族:“为了你们的安全,避开日本人的集中区,不要跟日军发生冲突”。“没过几天,英军就要回来。到时,日敌和为虎作伥的汉奸,都要受到严厉的处分。”接着说:“历年来在马来亚英勇抗战的游击队,和领导他们的英国军官,已奉命留守他们的防地。” 英军又通过盟军总部,向马共发出命令,不许马共和抗日军进城。 然而抗日军并不理会这些,各地独立队伍浩浩荡荡迈进了城市。他们接管了警察局,解除了敌伪警察的武装;接管了学校,重整教育课程;没收了敌产企业,归为人民所有;逮捕了一批汉奸走狗,拖到公审大会让人民裁决。马共成立了临时治安委员会,进而设立了各级人民委员会,形使行政职权。马共的威信达到前所未有的巅峰,人民期待它成立“马来亚人民共和国”。 马共中央代表陈田来了一趟新山,在百老汇戏院用华语和马来话,向群众发表了一次讲话。 然而英国人在争夺这片土地上也是竭尽所能,他们的奸细特务、亲英分子,四处走动,张挂布条,写着欢迎英国人回来的字样,深怕殖民主义者回不了马来亚。 日军入侵那年,英国人在马来亚已经逗留了155年。这是从殖民槟城算起,距离殖民最后的一块土地柔佛,也有27年,他算是一个老管家了。然而在这么悠久的治理当中,他始终没有建立起一支有效的军队保护人民,以至一个来自东洋的殖民新贵,59天就鹊巢鸠占了他的淘金窝。 英国人虽然投降了,却不甘失败,暗中支持马共抗日。等到终于轮到日本人也举起了白旗,英国人的嘴角露出贪婪的冷笑,看到了重归马来亚的希望。 可如今它似乎又要落入共产党的手里了,于是,他转动着那狡猾的脑袋,要从马共手里夺走这块肥肉。 这场战争,本质上是新旧殖民主义者抢夺殖民地的争霸战,人民是被践踏和鱼肉的对象。人民自动自发拿起枪杆,跟殖民主义者周旋到底的地方,才是真正的战场。英国人说他领导抗日军,鬼话!他只是要利用人民的力量打击日军,制造机会让他重温统治者的宝座。 到了1943年,战争进入了第二个年头,抗日军也站稳了脚部,日本人渐渐的不敢随便走出他们的基地,英国人...